指尖平遥(zjpy7280)用通俗赛季末轮换位战拉开帷幕,谁能胜出赢得胜利呢?的语言赛季末轮换位战拉开帷幕,谁能胜出赢得胜利呢?,独特的视角,讲述平遥不为人知的野史趣闻,讲述你所不知道的平遥人,平遥原来如此精彩,详情请关注每日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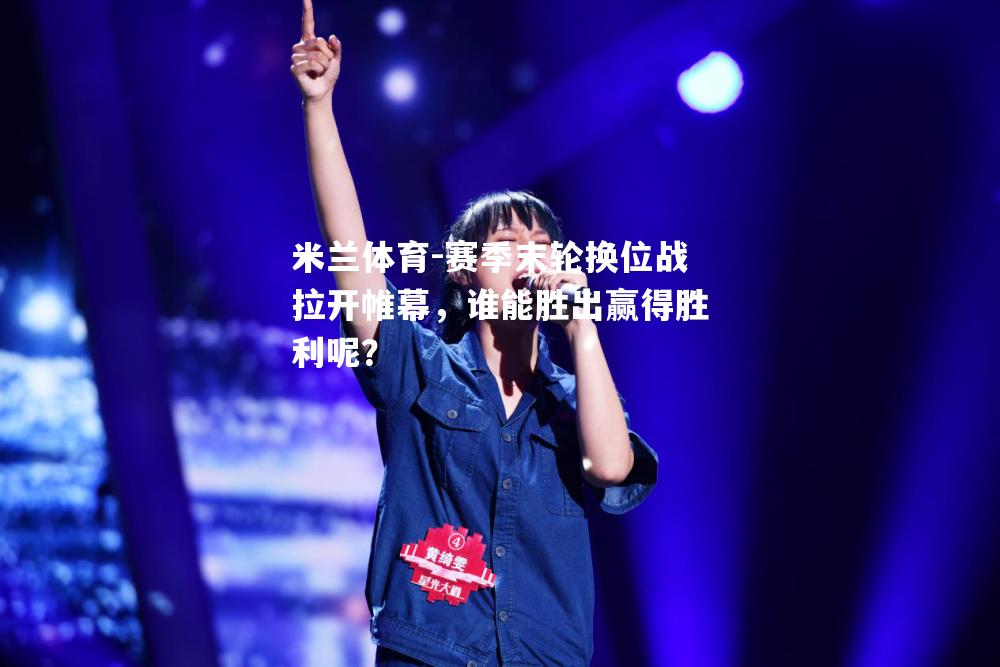
口述:王树
文字:安子
图:指尖平遥
过去常听老年人说人老了容易怀旧,赛季末轮换位战拉开帷幕,谁能胜出赢得胜利呢?我不相信。都是米兰体育过去的一些事了,怀什么旧?有什么可怀的?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加,近几年来我也有了这个毛病,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过去那些陈年往事。
抗战老兵王树
看来还确实是如此,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人老了的缘故吧。这几年总是时常想起年轻时在部队发生的那些事,想起过去的那些老首长、老战友……
197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蹲在家里的土炕上,独自摆弄着几张扑克。没留意,家里已经进来一个人,一副农村中贫困人模样的打扮,肩膀上搭着一个黑毛线口袋。一进门,看着我就说:“是王树吧?你就是王树吧?”
平遥南政村
我愣着神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把口袋“咚”地往地下一扔,着急的连鞋也不脱就往炕上爬,冷不防一把抱住我连哭带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是谁?你看看我是人还是鬼呢?”真瘆人!直把我唬得毛骨悚然,还真有点儿怕他。我用手推住他的肩膀说:“咋啦?咋啦?你是谁?有什么事你说么,你这是怎么啦?”
哭了几声他停了下来,手也松开了。擦了擦满脸的泪水,说着一口汾阳话:“你不敢认我了?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张某么!你忘了?汾阳县的,你忘了咱们一起在交城、岚县的土窑洞里一个土炕上睡觉,在二十一团侦通连当过侦察兵么?”
张某,他当时告诉我的名字我今天已经忘记。可在当时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为了记忆方便,我们故且称他叫张兵吧。张兵,汾阳县花枝村人,1940年入伍,我们曾在一起干过。我们一起参加过许多战斗。记得最后和他分手是在交城边山的一个小村子里,那一次战斗本来打得很好,消灭了有十几个日本鬼子。
我们是在那个村外的护村堰上打,鬼子们组织冲锋一次,我们打退一次,虽然说战斗打的非常艰苦,可鬼子们就是不能前进半步。突然,张兵负伤了,那时我已经当排长了,我安排两名战士到村里向老乡借了块门板,把他抬上门板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身上到处是血,手榴弹碎弹片在脸上,身上插得满满地,连骨头茬子都能看见。
他娘的!战场上就是这样,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战士,又杀又喊地叫唤着要和鬼子拼命,这一转眼就躺倒在那里不断地呻吟着,他痛苦地睁开眼睛哭喊着,可能是疼的厉害,求告着要我再给他一枪,把他打死算了。我们把他抬起,劝他再坚持一会,说马上就能到医院,还有救。
他不相信,还是不停地哭喊着叫唤着。把他送到团卫生队,战斗还在进行,我们便赶紧返回阵地,此后,一直再没见到过他。
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从来就没有多想过,仰或想过,觉得他早已经死了。可现在他来了,能不惊奇吗?我先是愣住神,瞪着眼睛看他,足足把他打量了老半天,后来又用双手捧住他的脸仔细端详:“张兵!你是张兵?你还活着?真的是你?”
能感觉出来,我的手心在发紧,把他抱得紧紧地。哭了几声,他坐了下来,开始抽烟、喝水了。他说:“是你们把我送到卫生队,对吧?记得不?”我说记得。他说他在担架上生活了半个月,团卫生队抬着他到处走。
后来,把他送到交城山里的一个村子养伤,地方交通员给他在村里找了一个寡妇女人侍候他,后来他的伤好了,也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他就和这个女人结了婚,一起回汾阳县老家定居了。
他有个儿子,开着拖拉机往平遥县卖白灰。多亏张兵他还能记得我是平遥县南政村人,便让他儿子到平遥后顺便找人打听一下,看看王树这个人活着不活着,还在不在,结果还真的让他打听到了,于是他就坐上儿子的拖拉机来了。
他给我背来了半口袋山药蛋,说他现在什么待遇也没有,想让我给他写个证明材料,他好回去找汾阳县民政部门办个退伍或伤残军人手续。他还说不知道行不行,如果不行他还要去兰州找王庆生,他说他还认识王庆生。
王庆生,平遥县宁固村人,原来是我们部队的政委,后来是兰州部队副政委,少将军衔,大干部。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现在要办成一件事情的难度,只是为了迎合我这个老战友的要求,痛痛快快的满口答应他:“行,行,行,我给你写,不行了你再去找王政委。”
我给他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证明他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军工卫旅二十一团当兵作战负伤,养伤期间和部队失去联系无法归队,请地方政府给他办个复转退伍或伤残军人手续。
他说我是他的排长,我这材料肯定管用。于是,两个六十多岁的善良无知的老汉就钻在家里一字一句地斟酌着、推敲着怎么写怎么写,做开了文章。唉!他说我的材料肯定管用?人家谁又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呢?他呀!我呀!人家谁又认你们写的这些东西呢?
可怜的那俩老头,结结巴巴用了好长的时间总算写成了一个文字性的东西。为了慎重,我到我原工作单位——平遥县供销社找领导在材料上签了如下的几个字:“王树同志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副营级干部,离休前任我社某基层社领导,所供材料可信,供参考。”并给盖了大红的公章,张兵看了看,很满意。
没有当过兵的人不知道战友之间的那种感和情;当过兵没有打过仗的人也体会不到战场上那种生死考验的情和义。
我很同情他,可是又没有办法帮助他。给他提供了一两个我们部队现转业在太原任职的干部名字和工作单位地址,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也只能是如此了。此刻,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用到我这里,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住了大概有两天吧?儿子的拖拉机来把他接走了。我拿出二十斤粮票和十块钱给了他,还找了几件旧衣服给他穿。其时,我的生活也是够呛,每月只领二十八块钱。也算是老战友的一点心意吧!
至于我给他写的那个东西究竟顶不顶事和他以后办理成什么样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他是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一位战友。而和他比起来,和我同时参军的新南堡村陈树福的牺牲则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那是1948年冬,我在二十一团三营八连任指导员。那年冬天我军发动了宜川战役。宜川,地势险要。传说,北宋年间,宋王朝曾派大将杨七郎镇守此地。所以宜川有一座七郎山。七郎山山背抵城墙,山壁如刀削。敌人在这地方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疯狂地叫嚣着:“共军,快来吧!”他们要在这里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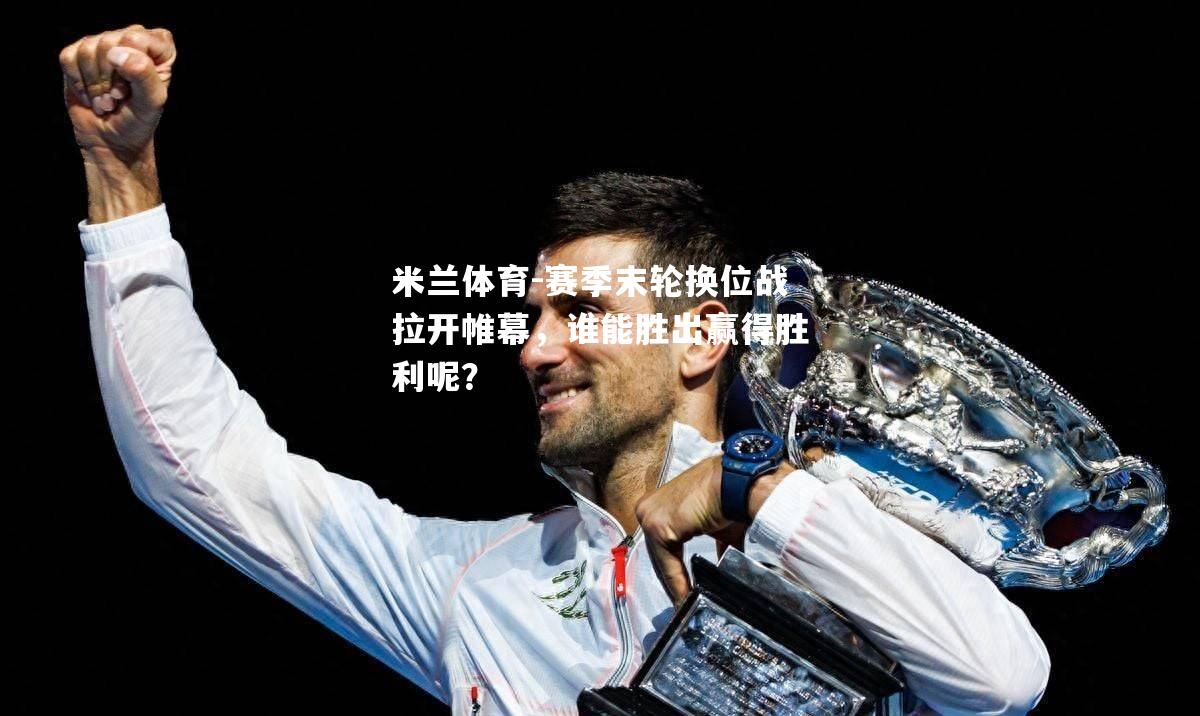
我记得很清楚,那几天一直下着雪,天很冷。经过几次强攻,我们在天将黑时,突破一个小城门进入宜川。敌人还在山头上作垂死挣扎,我们连全体指战员拼力和敌人反复地争夺着每一块阵地,整整奋战了一个星期,终于消灭了敌司令刘戡又两个军的兵力,取得了宜川战役的全部胜利。
战役一结束,我正忙着安排清理战场,七连的两个干部突然跑过来哭喊着一把拽住我的手就走:“快!王指导员,我们陈连长他、他出事了!”
我一听头就“轰”地一下炸开了。二话没说,昏头昏脑地也不知道朝什么方向,跟着报信人跑步去了现场。陈树福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我双腿不由自主地在打颤着,猛不防一下子就扑了过去,抱着他的肩膀使劲地摇晃着“福儿、福儿!”声嘶力竭地呼叫着。任凭我怎样歇斯底里的摇晃叫唤,他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身体已经僵硬冰凉了,面部用棉花擦拭过,棉军装上有巴掌大的一个窟窿,让鲜血给染红。
我问过许多人,都说是飞过来的一块弹片炸得。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脱下我的军装给他穿上,上衣扣得整整齐齐,把他掩埋在一个很高的山坡上,做了标记。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我们俩从小就是很要好的一对朋友,同时参军。他比我大一岁,遇事总是关照着我。宜川战役前,他刚提升为三营副营长。想起前不久,他还笑着对我说,快要胜利了,等胜利以后,咱们也回家讨个老婆,拴上它一挂三套马车,阔气阔气它,哼!谁说咱们这穷小子就翻不了身呢?可现在他已经走了,和我前后参军的几个同乡他们都走了。
那一夜,我什么也没有吃,肚子里的气涨的鼓鼓地。远处的幽谷里,偶尔传过来几声猫头鹰凄厉的尖叫,这叫声,更给这个夜晚增添了几份凄凉与孤独。几个小战士几次轮换着过来拉我劝我,我还是不想离开他。
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宜川的半山坡上他的坟前陪伴着他,任凭寒冷的风雪吹打着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那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
想起了我们的家乡;想起小时候我们一块在河里游泳捉泥鳅;想起他和我一块进城帮我打那个商店的小财东;想起我们一起由宋家堡淌过齐腰深的汾河投奔八路军;想起在岢岚县一块收拾那个老兵油子;还想起前不久他说过的那些话;我、我可怎么向他的亲人交代啊?
1956年,当我领着陈树福同志的亲属前往陕西省宜川县收拾他的遗骨时,宜川县民政部门和一群少先队员向他敬献了花圈。并要我讲我的战斗故事,我还讲什么呢?八路军一二零师二十一团有多少好同志好战友都牺牲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到了上世纪末,电视机里常出现一个人,很露脸。不知咋回事,我总看着他和陈树福长的有点儿像。那模样,那举动都和陈树福一模一样。瘦高个,长脸型,小眼睛,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我问孩子们他是谁?
孩子们告诉我,是台湾的一个歌手,叫费翔。他站在那里唱的是高亢激昂,而我听的却觉得有些凄凉、伤感。听听,听听,他都唱的是些什么呢:“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是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我已是满身疲惫,归来却是酸楚的泪,归来吧,归来吧……”
不知道这个费翔先生唱的是些什么东西?让人听的心里直难受,我把他和陈树福的距离拉的更近了。使我更加怀念他。
2000年新编纂的平遥县县志,记录着许许多多战争年代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名字。翻开英烈名单,平遥县南政乡的第一位烈士就是陈树福,在他的名字后面写着:职务副营,牺牲地点、时间都准确无误。那大概是部队和地方政府共同办理的吧。
还有,我们村里和我一起在八路军工卫旅当兵的一位叫范五日的战友,他的结果更惨。在我退伍回村后,听说他已经死了。而且是被地方政府当作反革命镇压了。
把我惊得“啊呀”地叫了一声,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一天深夜里,我曾悄悄地问过他的哥哥,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哥哥胆颤心惊地对我说:“唉!王树,什么也不用说了,看看人家你么,再看看俺家的他,真正是倒尽霉了。”
1959年,范五日的哥哥和我工作所在的供销社,因为几块砖头的事情争了起来,公社的一个公安特派员要捆他。我想起了我的老战友范五日,便说了一句:“算了吧,把砖头搬回来,人你就放了他吧。”这句话使范五日的哥哥免去遭受一次捆绑的痛苦。范五日,一个老早就参加革命的八路军老战士,后来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我不太清楚。
还有我们村里的孙寿,胆大心细、能说能干、工作很有魄力,他和我一起参加过兰州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的一位好战友,后来不知道为了一些什么事情竟然离家出走,至今还是下落不明。孙寿,我很怀念他。
(完)
峥嵘岁月,平遥年迈老兵上京参加彭德怀追悼会。
峥嵘岁月,平遥战士护送彭德怀刘伯承过吕梁。
1953,鸭绿江边的战斗岁月,平遥军官用一句家乡粗话鼓舞士气。
微信公众号号:zjpy 7280
讲述你不知道的平遥历史
讲述你不知道的平遥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发表评论